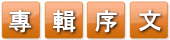從國展的名銜展開閱讀
「臺灣藝術研究院」舉辦的「台灣國展」規格頂尖,令人驚訝的她是民辦而非公辦的油畫比賽:耗費數千萬資金舉辦,參賽者遍及世界各地,評審制度完全不遜於公辦單一美術獎項規模,而這些都完全由私人自營自籌。這使我聯想起自己從大學到博士所就讀的西班牙馬德里大學美術學院,其傳承了跨越四個世紀的「皇家美術學院」 傳統。
西班牙「皇家美術學院」至今仍於創建時的馬德里原址經營美術學校及美術館,雖名為皇家,但並非我們認知的西班牙皇室經營項目,目前是私人基金會所經營擁有。「台灣國展」,同樣不是我們直覺認知的國家經營項目,跟「台灣國」、「國家展」都沒有關係。「臺灣藝術研究院」和院長的名銜亦是派頭極大,擔任領導者的林富男先生同時是發起人、贊助人,並擁有油畫家、政府文官最高十四職等官銜、集團總裁等多重身分。很早就聽聞名號見識其人,而我在高雄教學的第十七個年頭,才因緣際會真正交談與認識,受到已經舉辦十四年的「台灣國展」邀請擔任評審,過程感覺非常專業而愉悅,並且驚訝的發現:中生代的我可是評委當中最年輕的一位呢!
很榮幸受邀為本屆「台灣國展」作序。當時林院長邀請我為文作序,並且幽默地告訴我,
如果不會寫,他可以幫忙改,瞬間令我開懷大笑不已!難以簡短說明這麼大笑不已的關鍵,好好書寫整理是絕對合乎我們這個序文所探索的主旨:解疆域化。
林院長此言有其化解距離的幽默風格,自然無關乎禮貌尊重的匱乏,對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學者來說,論述意味著對感受的開發與探索,全面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撞擊與整合。所以評論不會是地位者的權力象徵,不會是應酬填充,不會是歌功頌德,更不會迴避隱藏真正的感受!在這樣的邏輯裡,只有前述我不會之狀態有寫不出來的可能,乃因為作為人而切斷跟真誠聯繫的管道。林院長幽默的直率言論,於整個「台灣國展」在台灣特殊政治環境下所隱含的解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課題,似乎又是一個有趣的應證。
解疆域化的藝術實踐
觀察「台灣國展」的發生背景與存在現象,和國展評審委員的前輩風貌,令人覺得相當有興味。在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中期,台灣經歷了從威權過渡為民主體制的轉型過程,而早在2004年已註冊在案的「台灣國展」名稱,是在1990年代轉型期後台灣意識正在社會興發的時期。
「台灣國展」可以任意解讀為台灣—國展,也可以是台灣國—展,雖則創立者並無此意,但此名稱的閱讀,在時代的脈絡上顯得自由而鬆動—「台灣」與「國」的關係,由法律與觀念的矛盾性(台灣只是中華民國憲法中的一個省份),轉變為情感與意識的正當性(成長於政治輪替年代的九零後已然形成天然獨的新生代)。
由社會演變來看,可說反映了時代性思維的自由流變。這個自由思維,除以上由名稱來解讀,更可探索以比賽機制名之為國展衍生的諸多身分、界域的流動,透過種種現象標誌了某一些原本在社會中僵固的轄域分界儼然被取消:民間主導辦國展,政界名流紛紛背書;政商主導辦藝術,藝界學者呼應參與;非官辦比賽,國內外反響熱烈—如此瓦解了民間、政府、藝界各擁勢力、標的相互角力的對峙。以政治人身份透過藝術推廣台灣,以企業人身份透過圖像接近土地,這種種都指向未被疆域化之流變特質。林院長以整體經營權控制策畫,進行無意識之社會性的總體藝術行為,綜而觀之,國展本身就是解疆域化的一場藝術實踐。
以「台灣國展」為名的叢林法則
命名為「台灣國展」卻由私人機構一手全權全力包辦,並且不向政府單位申請任何補助,完全不假國家資源之支援,不受政府行政制度之制約,於此項目上完全不同於前述相提並論之西班牙「皇家美術學院」—其在籌創演變過程中,努力通過國家規章並接受西班牙國王許多援助。
反觀「台灣國展」,不受政府條條框框制式規範,卻不是企圖找尋批判性、跳躍性、標新立異的特色,反而處處顯露正式化、章程化、規模化,國展評審委員更是各種前輩風貌,表面看似又一矛盾—否決公家機關制約卻又再次導入正統,實則在這種種表面看似自相矛盾之處,才更能解讀「台灣國展」的存在現象:以私辦之力更要超越官辦規格的宏觀視野和氣度,可以說是隱藏作者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說本人意識上不必然的認同,但更顯露出無意識的潛藏作用—擁有經濟執行力與政治影響力的財團,對體制面的意識形態之遊走操作,以及跨界之切換整合,於各式制度爭鬥範疇外再次獲得優游不同疆界之自由,無形中達成解疆域化之可能性。
在台灣,因緣複雜歷史背景而產生的後殖民轉型社會中,菁英—無論是政界或學界,大多仍然只是威權實質的包裝而已,究其行徑卻恰恰與菁英內涵完全的牴觸!菁英的基本特質應該包括:高難度的自我挑戰,不斷反省、覺知僵化與習性而跳脫,對於國家機器、社會制度的箝制自由精神感到身為己任而發聲、行動。而威權恰恰好相反,鞏固自己不受挑釁(所有異議都視為挑釁),不斷反省檢討別人,以制度抹煞個體,藉助國家機器馴化他者。在如此現實狀態之下,跨界的遊走,解疆域化的流變,都隱含有反菁英的情結,而其實這個反菁英的情結即是一種反僵化與反流俗的包裝!於是,「台灣國展」探觸了美術解疆域化,國展評審企及重建菁英結構,當學院與非學院同時受聘於「臺灣藝術研究院」為院士及國展顧問,也反轉了所謂的學院,消解了主客體原本的位置。
花費了這許多人力物力精神資金給獎的國展呀!這是「台灣國展」的時代性標誌,也是其對歷史意涵的爬梳建構,由機制上其代表了爭取藝術生態活化的真正叢林法則。
解疆域化與再疆域化
台灣國展的宗旨表明從全球徵件,但是強調在地化,主張台灣意識。2003年起台灣國展的徵選主題,即訂為「以台灣的人、事、物、景為主題,參賽者須對台灣的歷史、社會現狀或未來想像,透過藝術表現對台灣文化、土地、人文與環境營造的思維與視野,並能表徵台灣精神的作品」。這段徵選說明參賽主題須明確,乃要求以台灣的人、事、物、景作為表現題材。然而參賽者須對台灣的歷史、社會現狀或未來做理解,對台灣文化、土地與環境形成人文思維與關注視野,而後透過藝術表現傳達出來,並能表徵台灣精神—這段文字與其說是對參賽者的規範,更貼切地說乃是透過對藝術家的要求、界定,傳達出觀賞者的慾望、收藏者的想像、主辦方的期待。除可能對相同主題的反覆出現感覺了無新意,還預期能產生更深刻的創造性成果。
這徵選內容的表述其實很可能在創作者與其創作間產生疏離,此疏離並非第一段論述所探討,由於解疆域化而產生的表面矛盾,我個人認為恰恰相反,對參賽者所做的期待正是再疆域化的陷阱。一則此期許為人文厚度的累積,真正的藝術家須終其一生窮究探索,同時需要藝評家的發掘論述,之後及於觀賞者的理解。也就是說,以一人之力無法建構,而以藝術家每個人的自我探索透露出的集體無意識連結,假以時間的累積,方能見出端倪。
如今這個簡章說明與創作者的創作狀態是拘束而隔閡的,創作者或者無視,或者揣摩其義,都容易陷入僵化或者是疆域化的對應。再則,多元化的社會之可貴處即在於各種發聲的可能,不自陷於一個固定範疇,換言之,這個不簡單的比賽徵選簡章,蘊含著對後現代現象的台灣多元價值社會,一個統整性的期望值,亦即是對理想化過往的鄉愁。而正是這個對理想化過往的鄉愁,將解疆域化的一切,打回疆域化的原形。
對「理想化過往」的鄉愁
再聚焦於畫面的視覺傳達來談,欲達到人文厚度的養成與反思,須由命題的各個層面去摸索和撞擊,而表現出來的卻不一定是以台灣的符號為主題。如何說明呢?藉由義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在其著名小說《看不見的城市》 中的對話來想像:忽必烈皇帝問馬可波羅,為何述說了那麼多城市,卻有一個城市從未提到名字?馬可波羅回答:每當我在描繪一座城市時,我都在說著威尼斯。
繪畫表現可以滿眼盡是台灣景致,卻讓台灣缺席,也可以沒有台灣處處是台灣。以畫面表現風格為例來說明,用空靈飄渺的水墨山水畫描繪亞熱帶豔陽下的水田,將失去高溫多濕氣候帶來的黏膩身體感,斷裂了在地感受,只剩視覺形象的圖說,這就是滿眼台灣而沒有台灣,只是徒然回返視覺經驗的舊時餘蔭!而沒有台灣處處是台灣,最好的舉例就恰好是前述的例子反過來說,不在中國卻處處是中國,描繪著異域風光卻心懷固著的框架,無法真正看見。這樣的圖像也正代表了台灣意識並未被消化,或者說台灣主體意識尚未形成,而只是被符號化,在符號化的情形下,真正的情感反而被異化了。被異化的情感所能取暖的處所,於是不死的幽靈再次套上了多元化社會之前、被單一化的教育習性之與個人真實經驗牴觸的統整假象,名之為對理想化過往的鄉愁。許多網路票選結果特別揭示了這個狀態,嘗試的路不會是孰悉的風景,這也可解讀評審與網路票選結果落差的主因之一,其他當然還包括現場原作與數位圖像差異等種種因素。
2 Italo Calvino (2002). Las ciudades invisibles (Aurora Bernárdez, Trans.). Madrid: Siruela, S.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結語:由社會作用期待「台灣國展」未來
故此,「台灣國展」的源起,或者言其存在作用,得抽離學院中心的觀點來進行多方閱讀:不是從學術來看國展,而是從外交來看國展;不是從美術來看國展,而是從圖解來看國展,這是開端。「台灣國展」的頂峰很可能亦即是衰微的開端,這是歷史的必然法則,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乃因由解疆域化返回了疆域化的窠臼。
當一個社會需要台灣符號,一個政治需要台灣圖騰,誕生了「台灣國展」。徵選的題材是符號,主題的範疇定義是鄉愁,兩者之間的錯置,是過去的和現在的鴻溝。當國展持續經營,再疆域化能否迎來真正的解疆域化到來?若果「台灣國展」不再台灣了,那又會是甚麼樣的面貌?學術、美術、商業、政治,再疆域化的國展只能重複自己的曾經解疆域化的榮光?這個社會的惰性是如許之大,自由的面貌又再一次被收編,變形成為捍衛各自固守的領域範疇。
最後,從展名一路寫到網路,實在是直覺得這種種面貌極其豐富饒富旨趣,試著做了一些感受的整理爬梳與提問。本文代序作為對「台灣國展」結構與時代的解讀,彷彿是一個相當大的研究計畫的開題試寫,此次為文時間精力已達極限,期能有更多的關注「台灣國展」在台灣現代美術史上的這個重要標竿與現象。
西班牙馬德里大學 造型、技法與觀念博士班
創作理論博士
洪上翔
2017.06.12